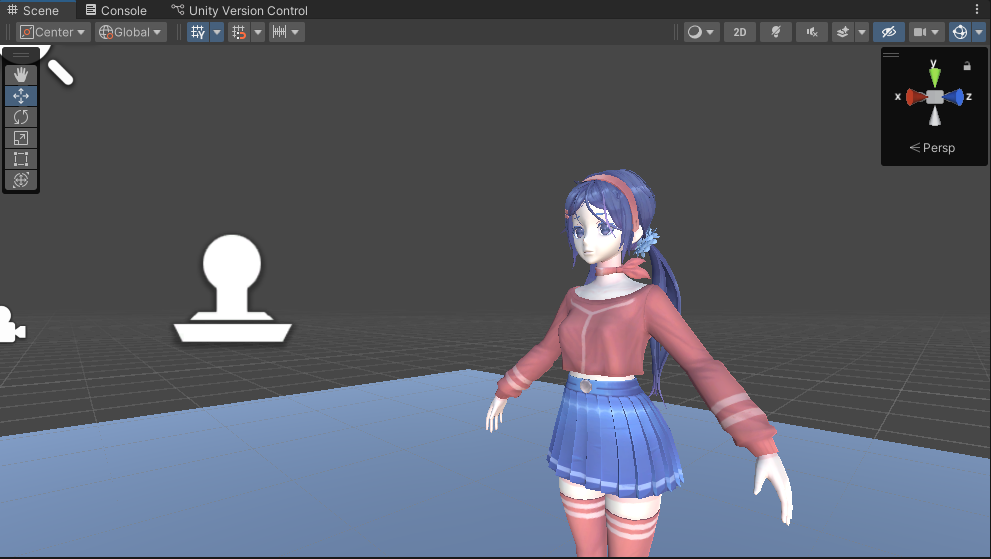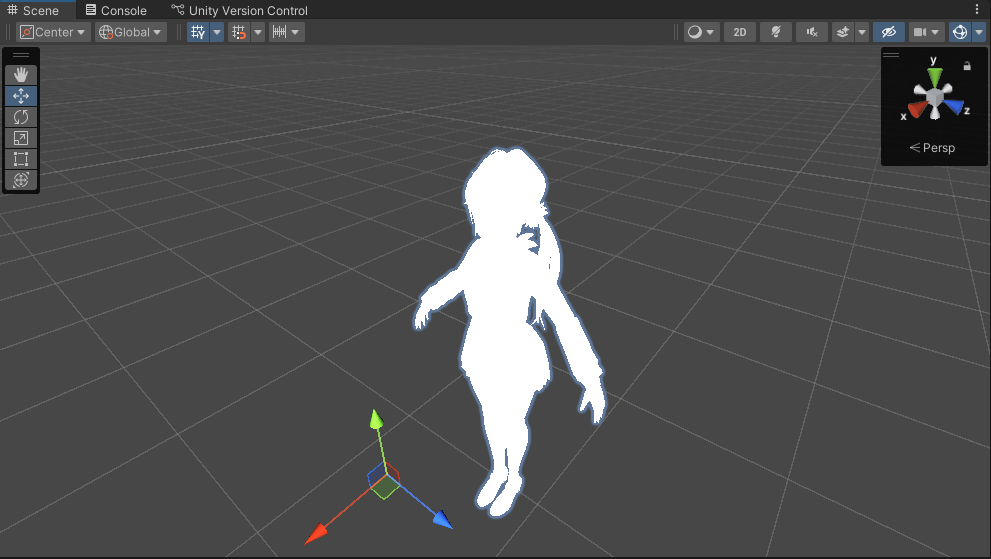《技术垄断》第一章 塔姆斯法老的批判
“他们接受的将是大量的信息,而不是老师的真传”——塔姆斯法老
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记载了埃及法老塔姆斯的故事,塔姆斯的朋友特乌斯发明了文字,并向塔姆斯炫耀,声称文字可以”增加埃及人的智慧,强化他们的记忆,找到了改善记忆和智慧的担保书”。塔姆斯提出了怀疑,”技艺发明人并不是评判发明利弊的最佳人选,只有使用者才能作出恰当的评判。识文断字的人可能不再使用记忆,而是成为健忘的人。他们接受的将是大量的信息,而不是老师的真传”。
塔姆斯的故事背后传达的是一个直到现在都很为重要的思想,那就是技术本身有其导向,而不受发明技术的人的控制,这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今天尤其重要。尽管特乌斯信誓旦旦地认为自己看到了文字的无限好处,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让人们都用文字来去做他认为重要的事情。特乌斯希望人们用文字来记录和传播真理,却忽视了文字是否会代替真理本身。换言之,技术在被创造出来之后,事实上就不再受发明者的意愿而控制了,技术不是中性的技术,它会按照自己内部的属性去改变一切。
弗洛伊德说:我们的发明只不过是手段的改进,目的却未见改善。毋庸置疑,技术在过去几百年取得的成就让每一个人惊叹,新技术必然会源源不断的出现,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暂时放下对于新技术的狂热,相对冷静、客观地衡量技术带来的利弊。也就是说,抛去手段,来仔细思考一下这些目的是否因为手段的改变而变得有所不同。
发明文字的人一定没有考虑到,文字会重塑我们的世界,而不仅仅是使“口头语言世界的智慧更为广泛地传播和更久地保存下来”。当然,文字做到了这些,但是事实上文字最后却改变了“真理”、“智慧”这些词汇原有的意义。或许在口头语言的时期,德高望重的老者记忆中的内容就是所谓的真理,但是文字出现后,有文字记载的内容将会取而代之。这些内容到底出自哪里根本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这两者之间出现冲突时,哪一种会被认为是真理。或许文字的出现还不能明显地体现出这些差别,但是在古登堡时代,这一切将会被改写。空前数量的印刷品远超过了一个人能掌握的所有内容,并且彻底地改变了我们对于“真理”的定义。
上述分析表明,一种媒介不仅仅是一种媒介,新旧媒介之间的竞争(例如口头语言和文字,以及印刷文化)也不仅仅是媒介的竞争。我们应当意识到,每一种媒介都有一种意识形态偏向,而媒介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背后的意识形态的竞争。在印刷机对手抄本发动攻击时,实际上还是背后的印刷文明对传统文明的攻击。每一种技术对于一些东西有着自己的想法,当他们与旧技术进行竞争时,实际上也是改变人们对于这种东西的理解的过程。现代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iPhone改变了我们对于智能手机的定义。在iPhone出来之前,我们可能对智能手机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是iPhone出来之后,我们认为,这就是智能手机,或者说,智能手机就应该是这样——一块完整的电容屏,不需要其他多余的按键。
尽管有很多用于特定环境的技术改进,他们大多数只对某一特定领域的内容产生影响。不过在很多研究该领域的科学家看来,技术和自然界一样,也是有生态的,一项技术不会独立地被创造,它的出现将对整个生态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一种新技术并不是什么东西的增减损益,它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一切。在现代,我们经常考虑的一件事是网课对于大学教育会带来哪些方面的改善或者坏处。但是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原因就在于,网课有可能重塑整个大学的教育体系(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大的趋势了,我敢说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看网课的时间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在大学课堂上听老师讲课的时间),被重塑后的体系甚至可能会以网课为主,大学课程的设立将建立在辅助网课的基础上。尽管大学的体系目前看上去和几十年前似乎是一样的,但是并不是说没有这种改变的可能性。所以当我们把目光稍微拉远,就会发现之前的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大学认为大学生就应该按照学院的安排,按照时间来一节课一节课地按部就班的学习,但是网课不这么认为。网课认为大学生就应该随时随地,想什么时候学任何内容,就可以去学。
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身边的一切,不仅仅是物质上,更包括我们日常的概念——也就是我们的世界观。跨越两千年,我们却更应该静下来倾听塔姆斯法老的告诫,因为我们已经来到所谓“技术垄断”的时代的十字街口。